
为纽约和长岛提供服务


W当我60年代初在博罗公园长大时,生活很简单。
我们是一个受庇护、受保护的一代。媒体不多,所以我们生活在泡沫中。我们从小就明白,如果我们学得好,努力工作,玩得好,交朋友,做所有正确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会长大,嫁给 talmidei chachamim,生下好孩子,他们会按照奥拉姆的道路行走。
至少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地方担心或迹象表明事情可能出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大屠杀后的一代,本应以如此与世隔绝的方式成长。但是我们做到了。我曾是时代课的模范学生。
我打得不错,学得很好。我努力奋斗,将目光投向了目标:嫁给一个高尚的查查姆,一个好人,并重建因组建家庭而失去的大门。
这就是发生的事情。神学院结束后我马上就结婚了,这正是我被教导的那样,然后我穿过韦拉扎诺桥到了所有年轻夫妇都去的地方,因为那是你应该去的地方。结婚第一年后,我生了一个男婴。就是应该的样子,对吧?
然后,十八个月后,1983年6月,我准时生下了一个小女孩。原本应该是这样... 只是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这次,我在怀孕结束时生病了,宝宝患上了病毒性肺炎,这种肺炎对抗生素没有反应。在她生命的前六周里,我的宝宝戴着呼吸器,为了活下去而英勇地战斗。
在医生和治疗之间,坐在宝宝的身边,我们正跑去拿brachos然后说Tehillim,向凯瓦里姆大喊大叫,在看着我们的小女孩为自己的生命而奋斗时尽我们所能。
为了应对我们所有的特菲洛,非常高的发烧和呼吸困难突然好转了。
我们的宝宝,我们称之为 Rochi,他脱下了呼吸器,医生们挠了挠头,说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孩子还活了下来。但是在我们带她出院回家之前,他们警告我们,尽管她还活着,但他们不知道这种疾病造成了什么损害。
“留意她。看看她的成长。” 他们一直在说。
我们做到了。我们密切地注视着她,看得越多,我们就越害怕。随着几周变成几个月,我一直注意到警告信号,医生的预约时间也增加了。
起初,我的儿科医生向我保证,由于早期的严重疾病,发育缓慢是正常的。但这是我的第二个孩子,我觉得出了点问题。Rochi 无法进行眼神交流,也无法独自抬起头。喂她很困难,她不停地哭了。她从来没有笑过,也从来没有笑过,而且她似乎与外界断绝了联系。
当我们过她的第一个生日时,Rochi... 什么也没做。然后医生做了检查,告诉我们她完全失聪了(缺少第八条脑神经,即从耳朵通向大脑的听觉神经),在法律上是盲人,自闭症,肌肉张力很低,可能永远无法行走。
我记得医生是如何建议我们把 Rochi 安置在家里的。他们告诉我:“你还年轻。”“只有二十二个。你会有更多的孩子,不要让这个孩子接管你的生活。有四次这样的诊断,她怎么能算什么?”
我将快进到三十九年后的今天。罗奇已婚,是三个漂亮、聪明、健康的孩子的母亲——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在十几岁的时候。她管理家庭,开车送孩子去他们需要去的地方,照顾他们的所有预约,做你期望妈妈做的一切。
怎么样?发生了什么?
答案:奥拉姆统治着世界的 Ribono shel。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人生座右铭是:永不言败。
***
早在1984年,我对诊断一无所知。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没有机构或服务,社区内部没有支持或资源,无处可寻求帮助、希望或指导。
我甚至无法描述那种完全孤独的感觉,没有一个电话号码可以拨打,没有一个资源可以尝试。这就是为什么Hamaspik和其他组织所做的工作如此重要的原因——它为年轻、惊恐的父母提供了一个可以求助的地方,有人来指导他们。
但是 Ribono shel Olam 是终极帮手。最后我找到了一位名叫阿黛尔·马克维茨的女士办公室的路,她以帮助聋哑儿童学习如何阅读和交流而闻名。
我带着一个十八个月大的孩子来到她的办公室,她撑不住自己,在整整四十五分钟的预约中,她尖叫着。最后,阿黛尔转向我说:“你的孩子被宠坏了!除非她学会以不同的方式行事,否则我无法与她合作。”
我感到震惊和恐惧。我的宝宝没有被宠坏;她有严重的残疾!
“她整夜都在睡觉吗?”阿黛尔按下。
“当然不是,” 我说。“她看不见或听不见。她哭是因为她很冷、很潮湿或饿了。我当然要照顾她。”
阿黛尔说:“除非你训练她整夜入睡,否则我无法和她一起工作。”
我受伤又愤怒,回家时感到心碎。我终于有希望为 Rochi 找到治疗师了,但她拒绝和她合作是因为她认为 Rochi 被宠坏了?
尽管如此,她的话在我脑海中浮现。那时我已经等着我的第三个孩子了,也许不必整晚醒来有两个孩子会有所帮助。
所以我做到了。我受过睡眠训练 Rochi。她花了十五晚才第一次睡到一整夜。
然后我给阿黛尔·马克维茨打电话说:“她整夜都在睡觉。”
她说:“好吧,看看那个。所以医生错了。”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了。“她仍然看不见或听不见。医生怎么错了?”
“好吧,” 她说,“他们说你不能教她任何东西。他们说她永远不会学习,你也永远不会从她身上赚到任何东西。但是看看你在短短两周内教了她什么。你教给她的是我们教给任何宝宝的第一件事!白天和黑夜的区别!”
然后她说,过去两年中所有令人沮丧的预言都化为乌有。她说:“你还要教她什么?”
那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实现时刻。如果医生错了,如果我能教我的孩子一件事,我就能教她一百万零一件事。
因此,我们开始了艰巨而艰巨的任务,试图教导一个聋、失明、自闭症的幼儿如何在世界上工作。
这并不容易。我们当中任何人通过渗透学获得的每一项技能都必须直接传授给 Rochi,因为她听不到或看不到周围发生的事情。
那怎么可能呢?
当然,首先是 siyata d'Shmaya。其次,我们一直在与时间赛跑。
我从来没有请过一天假。每一分钟都很重要,我们希望 Rochi 能够实现的每一点治疗和学习。如今,这已不是与有特殊需求的人合作的主流方法,但是当时,我们的资源很少,我们的治疗师和她的团队鼓励使用这种方法,努力实现我们能实现的最大目标。
在那些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服用 Rochi 进行治疗。Erev Shabbos、Erev Yom Tov、Chol Hamoed,整个夏天;日复一日。OT、PT,我们能找到的每种疗法,当然,都是我们自己资助的,因为没有服务
当时可用。经过几个月,我们发现她确实是个聪明的孩子。
我们教了她新东西,她学到了东西。我们教她的越多,她学到的越多。
当然,所有这一切的根本基础是特菲拉(tefillah),不断的辩护。我最狂热的 tefillah 是 Avinu Malkeinu,kera roah gezar dineinu。我恳求哈希姆,只删除一个诊断,删除一个诊断的一个方面。拜托,让她的生活更轻松一点。
事实是,他就是这样做的。耶稣不是一举过来的。它成了碎片。
***
第一个奇迹是眼睛。有一天晚上,我走进她的卧室想收拾东西,然后开了灯。当她睡觉时,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开灯或发出噪音的问题,因为她看不见太多,根本听不见。但是这次,当我开灯时,她醒来后睁开了眼睛。
于是我走了,回到医生那里。
我收到了很多不屑一顾的回应。“来吧,雅罗斯拉维茨夫人。她有多个残障人士。你只需要接受然后继续前进。”
但是当我告诉他们她在灯亮时醒来时,他们又做了一些测试。由于她无法告诉他们她看到了什么,他们使用了某种药物来测试眼睛,发现有一种眼镜可以帮助她。
我们很高兴能尝试它们,但我们还不知道她是否真的能从中看到更多。
然后是她的三岁生日。我为她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生日聚会 —— 并不是说我当时以为她自己会很感激,但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向她展示她和其他孩子一样经历过这样的经历。
我们唱了生日快乐,但她看上去什么都没有,没有听见,也看不见,即使戴眼镜也是如此。但是之后,我正在切蛋糕,她向前伸手舔了我手中的刀。
我很震惊。她怎么知道刀上有锦上添花?
当然,这让我又回到了医生办公室。这次我绝对坚持要有一些愿景,我恳求他们帮助我。“她听不见。如果她能看见,她就能口读了。”
哈希姆帮助了我们。通过更多的测试,他们意识到她的眼睛对齐不正确,手术可以帮助修复这个问题。
从第三次手术到四岁生日,罗奇做了三次手术,每次相隔六个月。而且变化是巨大的。
突然间,她的眼睛变直了。突然间,她对齐了,她开始互动和玩玩具。她开始四处走动。
我们有了一个新孩子。她学会了阅读英语和希伯来语。她学会了写作,学会了走路。她被一所给予了极大支持的学校录取——虽然我们为学校提供了影子,因此 Rochi 在教室里从来都不孤单,但他们确实让她感觉自己是事物的一部分。她上了一堂很棒的课,有很多朋友,并且成长和成长。
当然,也有挑战。学术方面很困难。我们仍在接受持续治疗。语言习得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因为根本没有听证会。
那时,我有点沉迷于想办法帮助 Rochi 听见。我们与医生进行了多次预约,尤其是纽约大学耳鼻喉科主任诺埃尔·科恩博士。他做了核磁共振成像和许多其他检查,但最终,他举起双手说:“听着,这种情况很少见。她缺少第八条脑神经,因此我们绝对无能为力。”
岁月流逝。我们继续向前迈进,她用力推动,但没错,她表现不错。等她上八年级的时候,我想说我们所有关于她是普通孩子的陈述,
一位年轻女士,一名女学生,除了听证和说话外,已经得到满足并得到答复。
她在走路。她正在学习。她有朋友。尽管我们花了将近八年的时间才进入那个阶段,但她的眼神交流还是接近 100%。但是她听不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通过写作与我们沟通)。
我在某处读到亚利桑那州的一位教授正在探索使用一种叫做耳朵的器官,这是一种耳内也能听见的器官,它被动物使用,尽管不是人类。我对此感到非常兴奋。也许 Rochi 能以某种方式从一种能激活她尿道的机器中受益?
那是个幻想。但是,嘿,我愿意尝试。
我联系了这位教授,他和我一样好奇,所以我安排去那里呆了三天。他自己做了一套核磁共振成像并承认了罗奇缺少这些器官的事实。然后他带我们进入一个装满机器的房间,每个 “助听器” 都差不多相当于一台冰箱的大小,他想方设法让她对声音做出反应。
什么都不起作用。
到三天结束时,我们一无所获。
第三天是星期五,我们安排在回家之前在酒店里度过沙博斯。当我丈夫打电话时,我开始在电炉上加热食物。对我来说,一切都变得太过分了。我分崩离析。
“我想回家,” 我哭了起来。“我不能再这样做了。好吧,所以她听不见...”
在电话的另一端,我丈夫陷入了困境。他想让我感觉好些,所以他说:“你猜怎么着?好消息。你在上周的中国拍卖会上赢了娃娃屋!”
那时我对娃娃屋没兴趣。我叫我丈夫把它放在地下室我下次再处理。
我们在 Shabbos 之后飞回了家。
第二天,我发现自己在 Amazing Savings 中,发现了这个全新的、神奇的现象:带轮子的手提箱!我很惊讶。Rochi 和我带着沉重的行李箱在机场穿梭——想象一下我们可以用这些行李箱吧!我决定买两个,一个给她,一个给我。但是后来我重新考虑了。Rochi 听不见。看来她永远不会。我为什么要买手提箱?她需要它干什么?
我停下来的时候正要离开商店。索拉,我告诉自己。你是否相信 Hashem 可以随时让 Rochi 恢复听力?你甚至不会买一个手提箱来证明你的 emunah 吗?
我转过身买了两个手提箱。当我回到家时,我把它们放在阁楼里,他们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一直待在那里。
有一天,当罗奇读十年级时,一位女士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有一位来自阿根廷的男人可以治愈听力损失,他将来威廉斯堡待一会儿。她说:“我想让你把女儿带到他身边。”“也许他能治好她。”
我没兴趣。我告诉她:“我希望我的女儿能得到治愈。”“但是你知道,她缺少听力所需的器官。这个人无能为力。”然后我挂断了电话。
但是那个女人坚持不懈。她给我丈夫打了电话。她又给我打了电话。
我仍然相信我们会为 Rochi 找个耶稣。我只是不相信它会通过医生解决。我已经走过那条路了。他们没能帮助我。
最终,在第四或第五个电话中,那个女人对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打个电话?在南美给他打电话,问问他是否认为自己能帮助你。”
我无法拒绝。我给这个人打电话解释了情况:我有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从出生起就严重失聪了。她没有第八大脑神经和耳蜗,助听器根本无法帮助她。
“你怎么知道她没有神经或耳蜗?”他回答,
我立刻说:“我已经做了很多次扫描和核磁共振成像。”
他对此提出了质疑。“你怎么知道她连一根这些器官的微观纤维都没有,太小了,无法出现在扫描中?”他问。
我没有答案。
他说:“听着,我要去布鲁克林。”“带你的女儿待三天。通常我坚持三周的协议,但你可以只来三天。看看三天后你能否发现任何变化。”
我愿意这样做,尽管 Rochi 在十年级时错过整整三天的学校并不容易。
这就是 “固化” 过程的样子:
我们去了临时诊所,这位扎着长马尾辫、几个耳环和几处纹身的 “医生” 围着一根带有闪光灯的大别针挥手致意。他会在她周围挥舞这个,然后过一会儿,他会点击她耳朵旁边的 Snapple 瓶盖然后他会问:“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
她没听见。所以他会派我们到等候室待一个小时,然后他会重复这个程序。一遍又一遍。整整三天。
到那段时间结束时,我绝对有了。我正要给安排预约的那位女士打电话,向她表示感谢,并告诉她这对我完全不起作用,而就在我拨号之前,它突然打中了我。
等等。你没试过。你没有检查她的听力是否有变化。
晚上十点,Rochi 正在楼下游戏室做作业。我拿起了最近的物品 —— 一个 Farberware 锅和一把汤勺 —— 然后我偷偷地走下地下室的楼梯躲到她看不见我的地方。
我选择在哪里?
只是...在娃娃屋娃娃后面。
因为当我在亚利桑那州歇斯底里的地狱时,在试图让 Rochi 听见三天失败之后,Ribono shel Olam 正在为耶稣设定道具。
在娃娃屋娃娃的后面,我拿起了起身和长勺子,然后我大声地发出了当声。
然而后罗奇惊讶地跳了起来。
我差点倒了吧。我已经完成了成百上千次听力测试,但是 Rochi 从来没有对任何声音做出过反应。现在我正在发声当声,她在回应!
当然,她不知道声音是什么 —— 她不知道是什么声音!是她坐下来回来做工了。
又发出了当声的声音。这次,她站起来四周环顾问,看看我在《娃娃娃屋后面》,拿着和长勺子。
她对我做到了。你在干什么?
她能读口语,所以我对她说:“你为什么问我?”
她表示自己的意思不知道。
我对她说:“我知道后来回到了办公场所。”我对她无能为力说,当你听见时刻的举手,因为她至今不知所措,听着会有什么。
她坐下来了,我又发出了当声,然后她举起了手。
我完全震惊了。
我给了我的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打了电话,他也是听力学家。我说:“坐下来向我保证,你不会笑我。”然后我告诉她,我已经接受过这个三天的电针对了 —— 事实就是这样 —— 而且 Rochi 现在正在回应花盆的当声了。
我的朋友说:“今晚我们都不会睡觉。穿好衣服。大约十五分钟后我来接你。让我们去曼哈顿,去我的隔音房间,给罗奇做个听力测试。”
在最后一刻,我随身携带花盆。
我们到了那里,我的朋友期望做了听力测试。Rochi 根本没有回复任何回应。
任何东西...除此之外,还有那个火锅。当我像在地下室一样发出了当声时,她听见了。
Ribono shel Olam 让我选择了那个和那把装满整个房子里所有物品的长勺,让我知道情况发生了变化。
第二天早上,我给了诺尔·科恩博士打了电话。作为人耳机的先锋,他举世闻名,但他一直坚称人耳机对罗奇不起作用,因为她缺少少耳机内部。
现在我坚称她已对声音做出了反应。
他直言不语地对我说:“你需要帮助。这不是答案的案例。”
我想,如果科恩医生无法帮助我们,我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找到二号医生。
我的朋友帮我做了研究,我们发现了保罗·基莱尼博士。他研究人体工耳机,曾在密歇根州安娜娜堡工专业制作。
那你觉得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放下了行李箱 —— 滚动的神奇储蓄手提箱 —— 然后出发前往密歇根州。
基莱尼博士进行了名为 “海角刺激试验” 的测试。他发现,确实有一些微小的纤维可以对声音做出反应。
经过两天的测试,他说:“听着,我愿尝试在她体内植物,但我明白不白。你有诺埃尔·科恩博士在纽约 —— 你为什么要来找我?”
我向他解释了发生了什么,他主动提示我们与科恩博士交谈话。我很害怕,但后来科恩博士给我打你说:“我听你一句话就是在探索瑞秋的探索。让我们再讨论一遍。”
是的我们回到了纽约大学的科恩博士那里,他同意,如果罗奇通过他要进行海角刺激测试,他将在那里给她植入人耳机。
十个月后,在1998年的普里姆,罗奇接见了她的第一个植物。四周后,在 bedikas chometz 日,他们开启了植入物——她对声音做出了反应。
Avinu Malkeinu,kera roah gear dineinu。Ribono shell Olam 可以做任何事情。
***
从那时起,发生了很多事情。罗奇开始说话。她的语言有改善。她十二年级毕业,上面有一年的神学院,就读于图罗。
她在另一边植入了第二种植物,增强了第一个植入物,当成了她的 shidduchim 的年龄,她已经是一个蓬勃发展、独立的年轻人。
Ribono shel Olam 在《他的无限制追捕》中给了她送了一个神奇的哈哈瓜,剩下的就是历史了。
人们经常问我:“你没有回来看医生,那我告诉他们错了?”
答案是肯定的。我从来没有想过那样做。部分原因是我没有时间做这件事,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如果我这样做了,我会觉得自己是在认识哈希姆因为我们做了那种精彩的阴影。
如果我说医生错了,从来没有像他们从一开始就想象象的那样,那我的意思是,chas v'shalom,这不是纯粹的奇迹,而且是哈希姆的错。
但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医生说得对。对她完全失踪了。她看不见。她非常自闭症。她的肌肉张力很低。
正是由于ribono shel Olam的勇气,Rochi才华得以克服每一个诊断,成了今天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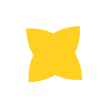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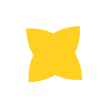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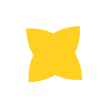










感官灵敏度低
中等感官敏感度
感官灵敏度高
非常高的感官灵敏度
0-15:感官敏感度低
感官灵敏度低
中等感官敏感度
感官灵敏度高
非常高的感官灵敏度
16-30:中等感官敏感度
感官灵敏度低
中等感官敏感度
感官灵敏度高
非常高的感官灵敏度
31-45:高感官灵敏度
感官灵敏度低
中等感官敏感度
感官灵敏度高
非常高的感官灵敏度
46-60:非常高的感官灵敏度